
今天(7.15)是俄国作家、剧作家契诃夫逝世的日子。他一生创作了七八百篇短篇小说。那些对人性的、市民的、社会的庖丁解牛式的描写,有种恶毒的幽默感。纳博科夫评价契诃夫的幽默:如果你看不到它的可笑,你也就感受不到它的可悲,因为可笑与可悲是浑然一体的。
本文作者童道明先生是研究契诃夫的专家,他一生挚爱契诃夫,他的身上,也散发着契诃夫式的温和、浪漫、深沉与悲悯。对於童先生,最快乐的事莫过於有人对他说,「我喜欢契诃夫」。

契诃夫的小说创作(节选)
文 | 童道明
契诃夫有句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姐妹。」这句话出自他1889年4月11日写给他哥哥亚历山大的一封信。而在三天前的4月8日,契诃夫在给苏沃林的信中,发表了同样的观点:「学着写得有才气,就是写得很简洁。」
有个实际的事例可以说明契诃夫对於简洁的追求。
1886年契诃夫写了篇小说《玫瑰色的袜子》。小说主人公索莫夫娶了个文化水平很低的老婆,但他并不介意。「怎么的?」索莫夫想,「想着谈谈学问上的事儿,我就去找纳塔丽娅·安德烈耶芙娜……很简单。」但《花絮》主编列依金发表这篇小说时,自作主张在小说结尾处加了一句:「不的,我不去,关於学问上的事儿,我可以跟男人们聊聊。他做了最後的决定。」尽管列依金是契诃夫的恩师,但契诃夫还是用幽默的口吻写信去表示了异议:「您加长了《玫瑰色的袜子》的结尾,我不反对因为多了一个句子而多得八戈比稿酬,但我以为,这裏与男人不相干……这裏说的仅仅是女人的事……」
契诃夫惜字如金,他的小说不少是开门见山的。
像《胖子与瘦子》(1883)——「在尼古拉叶夫斯基铁路的一个火车站上,有两个朋友,一个是胖子,一个是瘦子,碰见了。」
像《牵小狗的女人》(1899)——「听说,海边堤岸上出现了一张新面孔——一个牵小狗的女人。」
《牵小狗的女人》是契诃夫的一个少有的写爱情的小说,但小说裏见不到一点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肌肤相亲的场面,契诃夫只是告诉我们:「只是到了现在,当他头已经白了,他才真正用心地爱上了一个人。」然後就是写两个人分手之後的长相思,也写到了幽会(但没有用笔墨去描摹幽会的浪漫场面),而小说的结尾一句也是能让读者与两个相爱着的男女主人公一起「陷入遐想」的:
「似乎再过一会儿,就会找到办法了,新的美好的生活就要开始了。但他们两人心裏都清楚:距离幸福的目的地还很遥远,最复杂和困难的路程才刚刚开始。」
说契诃夫式的「简洁」,我还想拿小说《阿纽塔》(1886)作例。阿纽塔是学生公寓裏的一个女佣,二十五岁光景,她服侍的对象是个医学院三年级学生克留契科夫,她唯命是从地听从这位大学生的使唤,还「与他同居」。这天,克留契科夫已经动了将要辞退阿纽塔的念头,说:「你要知道,我们早晚要分手的。」而在这之前,契诃夫只用了短短的一段文字交代了阿纽塔的生活「前史」:
「在这六七年间,她辗转在这些公寓房子裏,像克留契科夫这样的大学生,她已经交往过五个。现在他们都已大学毕业,走上了人世间,当然,他们也像所有的有身份的人一样,早就忘记了她。」
我读到这裏,心裏升起了莫名的惆怅,同时也被契诃夫的简洁的笔法所感染。我由眼前的克留契科夫而想象到了阿纽塔之前侍候过的五个大学生的面影,又由那五个大学生的行状而想到克留契科夫「走上了人世间」後也会把阿纽塔忘得一干二净。
还在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念书的时候,契诃夫就开始文学创作,那时他都往幽默刊物投稿,而且署的都是笔名,用得最多的笔名是安东沙·契洪特,所以也有学者把这契诃夫初登文坛的时期称为「安东沙·契洪特时期」。而且研究者们都倾向於把《一个官员之死》(1883)、《胖子与瘦子》(1883)、《变色龙》(1885)、《普裏希别叶夫中士》(1885)等视为众多幽默小说中的杰作。
契诃夫是怀着什么样的人文精神与道德诉求踏上文坛的呢?这可以从他的两封书信中看出端倪。
1879年4月6日,契诃夫给弟弟米沙写信说:「弟弟,不是所有的米沙都是一个样子的。你知道应该在什么场合承认自己的渺小?在上帝面前,在智慧面前,在美面前,在大自然面前,但不是在人群面前。在人群中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
1889年1月7日,契诃夫写信给苏沃林说:「您写写他吧,写写这个青年人是如何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挤出去的。」
一个小小「文官」在一位将军面前的恐惧;一个「瘦子」在一个「胖子」面前的谄媚;一个「警官」在一只可能是将军家的「小狗」面前的出乖露丑;一个「一看见有人犯上就冒火」的「中士」,都丢掉了「人的尊严」,暴露了「身上的奴性」。契诃夫通过对於人身上的「奴性」的入木三分的揭露,张扬的正是维护人的尊严的人文主义精神。
除了「奴性」外,契诃夫还发现另一种人性的扭曲,那就是普通人不甘於当普通人的浮躁。因此,我以为在《一个官员之死》之前发表的《欣喜》(《喜事》,1883),也是值得一读的契诃夫早期创作中的佳作。
这个幽默作品写一个十四品文官是怎样因为在报纸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而欣喜欲狂的——「现在全俄罗斯都知道我了!我名扬全国了!」
而这位官职低得不能再低的文官是因为什么才名字上报的呢?原来是因为他是一桩交通事故的当事人而名字上了报纸的社会新闻!
後来契诃夫在小说《灯火》(1888)裏,也通过一个细节描写,对「小人物」不甘心当「小人物」的「小人物心理」做了令人悯笑的展示——「……还有一个叫克罗斯的人,想必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吧,他是多么深切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 以至於使出狠劲,将自己的名字用小刀往公园亭子栏杆上刻进去一寸深。」——这是俄罗斯式的「XXX到此一遊」。
这就是为什么高尔基能从契诃夫的这些幽默小品中,「听到他因为对那些不知道尊重自己人格的人的怜悯而发出的无望的叹息」。
「契诃夫小说选」的选家一般都不会漏掉《一个官员之死》等幽默小品名篇,我想除了它们的幽默品质、思想力度外,也因为它们可称契诃夫的简洁文笔的典範。
举知名度最高的《一个官员之死》作例。
在所有的幽默小品中,《一个官员之死》是最接近「黑色幽默」的。「打喷嚏总归不犯禁的」,但这个名叫切尔维亚科夫的小官,「在一个美好的傍晚」去看戏,因为打了个喷嚏,而惹了大麻烦。因为他怀疑唾沫星子可能喷到了坐在他前面的文职将军的身上,於是前後五次陪着小心,惶惶不安地向将军做出解释,赔礼道歉,而被这个小庶务官的反复赔罪搞得不耐烦的文职将军,终於铁青了脸向他大吼一声「滚出去!」而小官员听了这一声「滚出去」之後,「肚子裏似乎有什么东西掉下去了。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退到门口,走出去,慢腾腾地走着……他信步走到家裏,没脱掉制服,往长沙发上一躺,就此……死了」。
小说的结尾一点都不拖泥带水,却凸显了这个小官员之死的荒诞意味。
此外,契诃夫并没有在这个小官员的外部形态上花费笔墨,他的胆小怕事的人物性格与心理状态,也是通过人物本身的性格化的动作与言语加以展示的。
1886年,契诃夫写了一个像童话一样美丽的小说《玩笑》。那个名叫纳嘉的少女,为了能再次在风中听到「纳嘉,我爱你」这声神秘的呼唤,冒死从山顶向深渊滑去的少女,真是水灵得可爱。《玩笑》和1888年的《美女》说明契诃夫开始用心抒写女性之美了。
1886年最重要的作品无疑是《苦恼》。
《苦恼》的题辞引自《旧约全书》:「我拿我的烦恼向谁诉说?……」这篇小说的情节很简单:刚刚死去了儿子的马车夫姚纳,想把他的丧子之痛讲给别人听,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的诉说,最後,这位马车夫不得已,只好把他内心的痛苦讲给小母马听。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
小母马嚼着干草,听着,闻闻主人的手……
姚纳讲得有了劲,就把心裏的话统统讲给它听了……

这个出乎意外的结尾,当然也显示了契诃夫的幽默才华,但这个含有眼泪的幽默已经与他早期创作的供人解颐的幽默不可同日而语了。
然而,《苦恼》的价值主要还不是在於它表现了马车夫姚纳的苦恼,而是在於通过无人愿意倾听姚纳的苦恼这一事实,昭示了一个最令人苦恼的人间悲哀,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是20世纪文学的一个主题。而19世纪的契诃夫已经在自己的作品中触及了这个现代文学的主题。所以我们可以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契诃夫生活在19世纪,但他的思想属於20世纪。
自《苦恼》开端的表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的题旨,後来在契诃夫的作品中一再重复,成了成熟的契诃夫创作的一个潜在的主题。
而且这个主题是不断深化着的。如果说,在《苦恼》中,我们看到的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还来自人不肯与别人进行交流(别人不愿意听马车夫姚纳诉说他的丧子之痛),那到了後来,契诃夫想告诉我们:即便是存在着交流,甚至在充分的交流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还是存在隔膜,互相无法在心灵上沟通起来。
1886年,契诃夫也写有一篇幽默小说《一件艺术品》,在这个精致的小品中,契诃夫也用幽默的手法,展示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而契诃夫也正因为他的这种对於人生困顿的洞察力,使他的创作更具有时代精神。
因此,我们可以赞同德·斯·米尔斯基在《俄国文学史》中发表的一个观点:「在表现人与人之间无法逾越的隔膜和难以相互理解这一点上,无一位作家胜过契诃夫。」
契诃夫1887年写的小说裏,《信》值得拿出来专门说一说。
《信》得到过柴可夫斯基的激赏。这位作曲家读过《信》後给他弟弟写信说:「契诃夫在《新时报》上登的那篇小说昨天完全把我征服了。他果真是个大天才吧?」
这篇小说是围绕着一封「信」展开的。执事留彼莫夫的儿子彼得鲁希卡在外边上大学,有行为不检点的过失,执事便去央求修道院长写封信去教训教训儿子。修道院长写了封言辞十分严厉的信。神父看过信後劝执事别把这封信寄走,说「要是连自己的亲爹都不能原谅他,谁还会原谅他呢?」经神父这么一劝,执事开始思念儿子,「他尽想好的、温暖的、动人的……」最後便在修道院长写的「信後面添了幾句自己的话」,而「这点附言完全破坏了那封严厉的信」。
契诃夫用灵动的笔触,把执事留彼莫夫的心理活动及深藏在心裏的父爱描写得既真实又生动。
「书信」也每每出现在契诃夫的其他一些小说裏。试看小说名篇《万卡》(1886):九岁的万卡在一个鞋铺当学徒,备受店主欺凌,便给乡下的爷爷写信求救:「亲爱的爷爷,发发慈悲带我回家,我再也忍受不了啦!」但万卡在信封上写了「寄交乡下的祖父收」,是一封注定无法投递的死信。这让读者读後怆然有感,知道在契诃夫的幽默裏是闪动着泪光的。
《第六病室》(1892)也是契诃夫的一篇小说代表作。「书信」是在小说尾声出现的。此刻,拉京医生已经处於濒死状态——「随後一个农妇向他伸过手来,手裏捏着一封挂号信……」
这封没有展读的神秘的挂号信的内容,想必也应该和正直的拉京医生的思想相吻合的吧。
拉京医生在小说裏发表了不少激愤的言辞,最让人动容的是这一句:「您(指无端被关在‘第六病室’的智者伊凡·德米特裏奇)是个有思想、爱思考的人。在随便什么环境裏,您都能在自己的内心找到平静。那种极力要理解生活的、自由而深刻的思索,那种对人间无谓纷扰的十足蔑视——这是两种幸福,此外人类还从来没有领略过比这更高的幸福呢。」
19世纪俄国文坛有两大奇观——托尔斯泰的日记和契诃夫的书信。
契诃夫留下了四千多件信札,佔了他全部文学遗产的三分之一。在契诃夫的书信裏有他的真心情和大智慧。
在柴可夫斯基喜欢的契诃夫的小说中,还有同样是发表於1887年的《幸福》。这篇小说写两个牧羊人(一个年老的一个年轻的)和一个管家在一个草原之夜的幻想——对於幸福的幻想。而在契诃夫的描写中,草原上的天籁之音成了诗一般的交响:
「在朦胧的、凝固似的空气中,飘荡着单调的音响,这是草原之夜的常态。蟋蟀不停地发出唧唧声,鹌鹑在鸣叫,离羊群一裏开外的山谷裏,流着溪水,长着柳树,年轻的夜莺在无精打采地啼啭。」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另一位俄罗斯大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1875—1943),也是契诃夫作品的崇拜者,他的研究者说,最让这位作曲家倾倒的,是「美妙的契诃夫的音乐性」。
最早指出契诃夫作品的音乐性的,是俄罗斯戏剧家梅耶荷德,他曾称契诃夫的剧本《樱桃园》「像柴可夫斯基交响乐」。
当然,音乐性不仅来自声响,同样也来自张弛有致的节奏,甚至来自有意味的无声的交响。请看《幸福》是如何结尾的:
「老人和山卡(即两个一老一少的牧羊人——引者)各自拄着牧杖,立在羊群两端,一动也不动,像是苦行僧在祷告。他们聚精会神地思索着。他们不再留意对方,各人生活在各人的生活裏。那些羊也在思索……」

注:①指基督教的习俗:圣诞节前夜小孩们举着用簿纸糊的星星走来走去。
本文节选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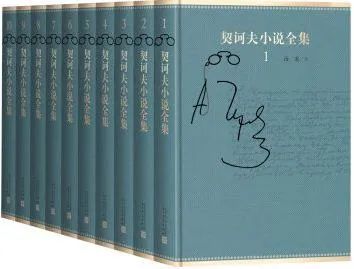
《契诃夫小说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